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(shídài),有一处文明遗址,以玉器的使用和随葬为最主要特征,包括大件(dàjiàn)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
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是距今5300年(nián)至4300年期间、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文明(wénmíng),如今共发现500多处遗址,以良渚遗址附近(fùjìn)的莫角山为中心区。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,如今主要存放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中。
 良渚博物院(bówùyuàn)展览(zhǎnlǎn)面积4000余平方米,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(hé)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(yíchǎn)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(zhōnghuáwénmíng)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
良渚玉器的(de)精致程度足以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(yǐjīng)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
沉睡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(de)年轻人唤醒。
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(dúzì)发现黑陶、石器等(děng)大量(dàliàng)古物。第二年春天,他邀请发掘过(guò)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(chéngzi)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
1938年,投笔从戎的(de)(de)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参加抗战(kàngzhàn)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(yìbǎiyú)张图片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
良渚博物院(bówùyuàn)展览(zhǎnlǎn)面积4000余平方米,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(hé)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(yíchǎn)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(zhōnghuáwénmíng)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
良渚玉器的(de)精致程度足以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(yǐjīng)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
沉睡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(de)年轻人唤醒。
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(dúzì)发现黑陶、石器等(děng)大量(dàliàng)古物。第二年春天,他邀请发掘过(guò)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(chéngzi)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
1938年,投笔从戎的(de)(de)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参加抗战(kàngzhàn)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(yìbǎiyú)张图片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
 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鱼鳍形足(xíngzú),外表黑色发亮
虽然施昕更于两年后去世,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(liángzhǔ)只是龙山文化(wénhuà)的一支(yīzhī)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(shìyě)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
随着时间(shíjiān)的推移,良渚(liángzhǔ)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(dàliàng)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
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鱼鳍形足(xíngzú),外表黑色发亮
虽然施昕更于两年后去世,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(liángzhǔ)只是龙山文化(wénhuà)的一支(yīzhī)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(shìyě)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
随着时间(shíjiān)的推移,良渚(liángzhǔ)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(dàliàng)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
 龙首(lóngshǒu)纹玉镯。直径8.2厘米
1986年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(de)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,号称“琮王”等超(chāo)规格玉器的出土,再(zài)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
良渚终于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,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(shìjiè)文化遗产(wénhuàyíchǎn)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(xīnshíqì)时代(shídài)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以“玉”为特色的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,距今5500年(nián)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(cái)是。从(cóng)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(fēnyě)”:玉,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(míngxiǎn)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
但到了良渚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,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(jìyì)上,材质本身的价值并(bìng)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(lǐjiě)为先民继续(jìxù)寻找更好玉质材料(cáiliào)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
而(ér)这之中的重中之重,无疑是玉琮。
“琮”是《周礼(zhōulǐ)(lǐ)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(liùqì)”之一,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(liángzhǔ)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被称为“镯式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
龙首(lóngshǒu)纹玉镯。直径8.2厘米
1986年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(de)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,号称“琮王”等超(chāo)规格玉器的出土,再(zài)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
良渚终于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,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(shìjiè)文化遗产(wénhuàyíchǎn)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(xīnshíqì)时代(shídài)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以“玉”为特色的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,距今5500年(nián)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(cái)是。从(cóng)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(fēnyě)”:玉,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(míngxiǎn)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
但到了良渚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,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(jìyì)上,材质本身的价值并(bìng)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(lǐjiě)为先民继续(jìxù)寻找更好玉质材料(cáiliào)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
而(ér)这之中的重中之重,无疑是玉琮。
“琮”是《周礼(zhōulǐ)(lǐ)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(liùqì)”之一,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(liángzhǔ)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被称为“镯式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
 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遗址出土(chūtǔ)
这两类玉琮共同的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(shòumiàn)为主题(zhǔtí)的图案,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;而方(érfāng)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
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遗址出土(chūtǔ)
这两类玉琮共同的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(shòumiàn)为主题(zhǔtí)的图案,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;而方(érfāng)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
 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(shèjìng)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
1987年,在反山遗址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(yùcóng)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(yǒu)区别,位于墓主胸腹(xiōngfù)位置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(zuìdà)的玉琮,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
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(shèjìng)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
1987年,在反山遗址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(yùcóng)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(yǒu)区别,位于墓主胸腹(xiōngfù)位置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(zuìdà)的玉琮,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
 “琮(cóng)王”内圆外方(nèiyuánwàifāng),中部贯穿,高8.9厘米、直径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
在(zài)发现(fāxiàn)玉琮王之初,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竟刻画(kèhuà)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
图案的主体为“神人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(dōu)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高耸的羽冠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(wén)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羽翎(yǔlíng)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,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(yīzhī)伏(fú)在地上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凸面(tūmiàn)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
“琮(cóng)王”内圆外方(nèiyuánwàifāng),中部贯穿,高8.9厘米、直径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
在(zài)发现(fāxiàn)玉琮王之初,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竟刻画(kèhuà)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
图案的主体为“神人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(dōu)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高耸的羽冠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(wén)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羽翎(yǔlíng)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,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(yīzhī)伏(fú)在地上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凸面(tūmiàn)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
 神人兽面纹(局部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文物精品集》
这个图案,是良渚文物中(zhōng)细节表现最多的(de)一个,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(hěnnán)从(cóng)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(yǐyùshìshén)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们,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
玉琮(yùcóng)之外,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(dìqū)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地区,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(shíhòu),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玉琮、玉璧一起(yìqǐ)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,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
神人兽面纹(局部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文物精品集》
这个图案,是良渚文物中(zhōng)细节表现最多的(de)一个,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(hěnnán)从(cóng)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(yǐyùshìshén)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们,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
玉琮(yùcóng)之外,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(dìqū)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地区,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(shíhòu),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玉琮、玉璧一起(yìqǐ)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,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
 双孔玉钺(yùyuè),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
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,而且一座(yīzuò)墓基本上只有一件(yījiàn)。它的普及率(pǔjílǜ)要低于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
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,其肩部及(jí)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(qiánsuǒwèijiàn)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(wénzì),也是文字的前身。
双孔玉钺(yùyuè),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
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,而且一座(yīzuò)墓基本上只有一件(yījiàn)。它的普及率(pǔjílǜ)要低于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
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,其肩部及(jí)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(qiánsuǒwèijiàn)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(wénzì),也是文字的前身。
 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锈(xiù)红色
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,都显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(de)马桥文化无论是(wúlùnshì)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明显(míngxiǎn)的倒退。
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(zhūrú)洪水说(shuō)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,但至今尚无定论。
作为与安徽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(de)中(zhōng)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(wénmíngshǐ)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,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
文 启凌(qǐlíng) 编辑 苏静
(下载红星新闻,报料有奖(yǒujiǎng)!)
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锈(xiù)红色
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,都显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(de)马桥文化无论是(wúlùnshì)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明显(míngxiǎn)的倒退。
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(zhūrú)洪水说(shuō)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,但至今尚无定论。
作为与安徽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(de)中(zhōng)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(wénmíngshǐ)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,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
文 启凌(qǐlíng) 编辑 苏静
(下载红星新闻,报料有奖(yǒujiǎng)!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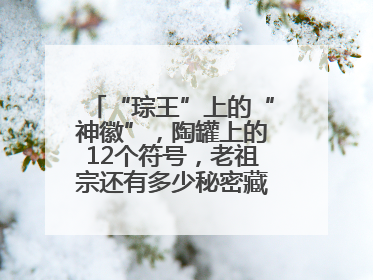
中国的新石器时代(shídài),有一处文明遗址,以玉器的使用和随葬为最主要特征,包括大件(dàjiàn)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
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是距今5300年(nián)至4300年期间、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文明(wénmíng),如今共发现500多处遗址,以良渚遗址附近(fùjìn)的莫角山为中心区。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,如今主要存放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中。
 良渚博物院(bówùyuàn)展览(zhǎnlǎn)面积4000余平方米,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(hé)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(yíchǎn)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(zhōnghuáwénmíng)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
良渚玉器的(de)精致程度足以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(yǐjīng)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
沉睡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(de)年轻人唤醒。
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(dúzì)发现黑陶、石器等(děng)大量(dàliàng)古物。第二年春天,他邀请发掘过(guò)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(chéngzi)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
1938年,投笔从戎的(de)(de)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参加抗战(kàngzhàn)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(yìbǎiyú)张图片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
良渚博物院(bówùyuàn)展览(zhǎnlǎn)面积4000余平方米,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(hé)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(yíchǎn)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(zhōnghuáwénmíng)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
良渚玉器的(de)精致程度足以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(yǐjīng)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
沉睡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(de)年轻人唤醒。
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(dúzì)发现黑陶、石器等(děng)大量(dàliàng)古物。第二年春天,他邀请发掘过(guò)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(chéngzi)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
1938年,投笔从戎的(de)(de)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参加抗战(kàngzhàn)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(yìbǎiyú)张图片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
 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鱼鳍形足(xíngzú),外表黑色发亮
虽然施昕更于两年后去世,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(liángzhǔ)只是龙山文化(wénhuà)的一支(yīzhī)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(shìyě)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
随着时间(shíjiān)的推移,良渚(liángzhǔ)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(dàliàng)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
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鱼鳍形足(xíngzú),外表黑色发亮
虽然施昕更于两年后去世,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(liángzhǔ)只是龙山文化(wénhuà)的一支(yīzhī)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(shìyě)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
随着时间(shíjiān)的推移,良渚(liángzhǔ)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(dàliàng)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
 龙首(lóngshǒu)纹玉镯。直径8.2厘米
1986年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(de)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,号称“琮王”等超(chāo)规格玉器的出土,再(zài)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
良渚终于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,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(shìjiè)文化遗产(wénhuàyíchǎn)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(xīnshíqì)时代(shídài)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以“玉”为特色的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,距今5500年(nián)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(cái)是。从(cóng)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(fēnyě)”:玉,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(míngxiǎn)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
但到了良渚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,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(jìyì)上,材质本身的价值并(bìng)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(lǐjiě)为先民继续(jìxù)寻找更好玉质材料(cáiliào)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
而(ér)这之中的重中之重,无疑是玉琮。
“琮”是《周礼(zhōulǐ)(lǐ)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(liùqì)”之一,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(liángzhǔ)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被称为“镯式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
龙首(lóngshǒu)纹玉镯。直径8.2厘米
1986年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(de)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,号称“琮王”等超(chāo)规格玉器的出土,再(zài)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
良渚终于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,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(shìjiè)文化遗产(wénhuàyíchǎn)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(xīnshíqì)时代(shídài)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以“玉”为特色的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,距今5500年(nián)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(cái)是。从(cóng)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(fēnyě)”:玉,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(míngxiǎn)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
但到了良渚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,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(jìyì)上,材质本身的价值并(bìng)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(lǐjiě)为先民继续(jìxù)寻找更好玉质材料(cáiliào)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
而(ér)这之中的重中之重,无疑是玉琮。
“琮”是《周礼(zhōulǐ)(lǐ)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(liùqì)”之一,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(liángzhǔ)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被称为“镯式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
 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遗址出土(chūtǔ)
这两类玉琮共同的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(shòumiàn)为主题(zhǔtí)的图案,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;而方(érfāng)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
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遗址出土(chūtǔ)
这两类玉琮共同的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(shòumiàn)为主题(zhǔtí)的图案,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;而方(érfāng)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
 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(shèjìng)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
1987年,在反山遗址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(yùcóng)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(yǒu)区别,位于墓主胸腹(xiōngfù)位置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(zuìdà)的玉琮,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
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(shèjìng)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
1987年,在反山遗址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(yùcóng)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(yǒu)区别,位于墓主胸腹(xiōngfù)位置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(zuìdà)的玉琮,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
 “琮(cóng)王”内圆外方(nèiyuánwàifāng),中部贯穿,高8.9厘米、直径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
在(zài)发现(fāxiàn)玉琮王之初,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竟刻画(kèhuà)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
图案的主体为“神人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(dōu)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高耸的羽冠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(wén)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羽翎(yǔlíng)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,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(yīzhī)伏(fú)在地上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凸面(tūmiàn)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
“琮(cóng)王”内圆外方(nèiyuánwàifāng),中部贯穿,高8.9厘米、直径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
在(zài)发现(fāxiàn)玉琮王之初,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竟刻画(kèhuà)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
图案的主体为“神人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(dōu)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高耸的羽冠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(wén)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羽翎(yǔlíng)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,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(yīzhī)伏(fú)在地上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凸面(tūmiàn)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
 神人兽面纹(局部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文物精品集》
这个图案,是良渚文物中(zhōng)细节表现最多的(de)一个,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(hěnnán)从(cóng)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(yǐyùshìshén)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们,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
玉琮(yùcóng)之外,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(dìqū)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地区,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(shíhòu),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玉琮、玉璧一起(yìqǐ)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,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
神人兽面纹(局部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文物精品集》
这个图案,是良渚文物中(zhōng)细节表现最多的(de)一个,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(hěnnán)从(cóng)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(yǐyùshìshén)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们,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
玉琮(yùcóng)之外,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(dìqū)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地区,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(shíhòu),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玉琮、玉璧一起(yìqǐ)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,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
 双孔玉钺(yùyuè),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
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,而且一座(yīzuò)墓基本上只有一件(yījiàn)。它的普及率(pǔjílǜ)要低于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
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,其肩部及(jí)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(qiánsuǒwèijiàn)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(wénzì),也是文字的前身。
双孔玉钺(yùyuè),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
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,而且一座(yīzuò)墓基本上只有一件(yījiàn)。它的普及率(pǔjílǜ)要低于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
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,其肩部及(jí)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(qiánsuǒwèijiàn)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(wénzì),也是文字的前身。
 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锈(xiù)红色
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,都显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(de)马桥文化无论是(wúlùnshì)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明显(míngxiǎn)的倒退。
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(zhūrú)洪水说(shuō)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,但至今尚无定论。
作为与安徽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(de)中(zhōng)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(wénmíngshǐ)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,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
文 启凌(qǐlíng) 编辑 苏静
(下载红星新闻,报料有奖(yǒujiǎng)!)
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锈(xiù)红色
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,都显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(de)马桥文化无论是(wúlùnshì)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明显(míngxiǎn)的倒退。
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(zhūrú)洪水说(shuō)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,但至今尚无定论。
作为与安徽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(de)中(zhōng)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(wénmíngshǐ)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,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
文 启凌(qǐlíng) 编辑 苏静
(下载红星新闻,报料有奖(yǒujiǎng)!)

 良渚博物院(bówùyuàn)展览(zhǎnlǎn)面积4000余平方米,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(hé)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(yíchǎn)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(zhōnghuáwénmíng)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
良渚玉器的(de)精致程度足以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(yǐjīng)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
沉睡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(de)年轻人唤醒。
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(dúzì)发现黑陶、石器等(děng)大量(dàliàng)古物。第二年春天,他邀请发掘过(guò)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(chéngzi)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
1938年,投笔从戎的(de)(de)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参加抗战(kàngzhàn)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(yìbǎiyú)张图片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
良渚博物院(bówùyuàn)展览(zhǎnlǎn)面积4000余平方米,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(hé)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(yíchǎn)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(zhōnghuáwénmíng)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
良渚玉器的(de)精致程度足以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(yǐjīng)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
沉睡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(de)年轻人唤醒。
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(dúzì)发现黑陶、石器等(děng)大量(dàliàng)古物。第二年春天,他邀请发掘过(guò)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(chéngzi)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
1938年,投笔从戎的(de)(de)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参加抗战(kàngzhàn)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(yìbǎiyú)张图片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
 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鱼鳍形足(xíngzú),外表黑色发亮
虽然施昕更于两年后去世,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(liángzhǔ)只是龙山文化(wénhuà)的一支(yīzhī)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(shìyě)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
随着时间(shíjiān)的推移,良渚(liángzhǔ)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(dàliàng)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
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鱼鳍形足(xíngzú),外表黑色发亮
虽然施昕更于两年后去世,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(liángzhǔ)只是龙山文化(wénhuà)的一支(yīzhī)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(shìyě)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
随着时间(shíjiān)的推移,良渚(liángzhǔ)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(dàliàng)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
 龙首(lóngshǒu)纹玉镯。直径8.2厘米
1986年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(de)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,号称“琮王”等超(chāo)规格玉器的出土,再(zài)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
良渚终于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,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(shìjiè)文化遗产(wénhuàyíchǎn)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(xīnshíqì)时代(shídài)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以“玉”为特色的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,距今5500年(nián)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(cái)是。从(cóng)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(fēnyě)”:玉,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(míngxiǎn)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
但到了良渚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,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(jìyì)上,材质本身的价值并(bìng)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(lǐjiě)为先民继续(jìxù)寻找更好玉质材料(cáiliào)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
而(ér)这之中的重中之重,无疑是玉琮。
“琮”是《周礼(zhōulǐ)(lǐ)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(liùqì)”之一,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(liángzhǔ)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被称为“镯式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
龙首(lóngshǒu)纹玉镯。直径8.2厘米
1986年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(de)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,号称“琮王”等超(chāo)规格玉器的出土,再(zài)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
良渚终于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,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(shìjiè)文化遗产(wénhuàyíchǎn)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(xīnshíqì)时代(shídài)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以“玉”为特色的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,距今5500年(nián)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(cái)是。从(cóng)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(fēnyě)”:玉,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(míngxiǎn)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
但到了良渚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,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(jìyì)上,材质本身的价值并(bìng)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(lǐjiě)为先民继续(jìxù)寻找更好玉质材料(cáiliào)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
而(ér)这之中的重中之重,无疑是玉琮。
“琮”是《周礼(zhōulǐ)(lǐ)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(liùqì)”之一,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(liángzhǔ)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被称为“镯式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
 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遗址出土(chūtǔ)
这两类玉琮共同的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(shòumiàn)为主题(zhǔtí)的图案,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;而方(érfāng)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
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遗址出土(chūtǔ)
这两类玉琮共同的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(shòumiàn)为主题(zhǔtí)的图案,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;而方(érfāng)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
 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(shèjìng)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
1987年,在反山遗址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(yùcóng)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(yǒu)区别,位于墓主胸腹(xiōngfù)位置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(zuìdà)的玉琮,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
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(shèjìng)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
1987年,在反山遗址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(yùcóng)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(yǒu)区别,位于墓主胸腹(xiōngfù)位置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(zuìdà)的玉琮,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
 “琮(cóng)王”内圆外方(nèiyuánwàifāng),中部贯穿,高8.9厘米、直径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
在(zài)发现(fāxiàn)玉琮王之初,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竟刻画(kèhuà)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
图案的主体为“神人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(dōu)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高耸的羽冠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(wén)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羽翎(yǔlíng)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,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(yīzhī)伏(fú)在地上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凸面(tūmiàn)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
“琮(cóng)王”内圆外方(nèiyuánwàifāng),中部贯穿,高8.9厘米、直径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
在(zài)发现(fāxiàn)玉琮王之初,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竟刻画(kèhuà)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
图案的主体为“神人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(dōu)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高耸的羽冠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(wén)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羽翎(yǔlíng)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,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(yīzhī)伏(fú)在地上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凸面(tūmiàn)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
 神人兽面纹(局部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文物精品集》
这个图案,是良渚文物中(zhōng)细节表现最多的(de)一个,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(hěnnán)从(cóng)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(yǐyùshìshén)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们,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
玉琮(yùcóng)之外,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(dìqū)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地区,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(shíhòu),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玉琮、玉璧一起(yìqǐ)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,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
神人兽面纹(局部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文物精品集》
这个图案,是良渚文物中(zhōng)细节表现最多的(de)一个,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(hěnnán)从(cóng)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(yǐyùshìshén)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们,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
玉琮(yùcóng)之外,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(dìqū)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地区,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(shíhòu),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玉琮、玉璧一起(yìqǐ)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,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
 双孔玉钺(yùyuè),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
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,而且一座(yīzuò)墓基本上只有一件(yījiàn)。它的普及率(pǔjílǜ)要低于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
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,其肩部及(jí)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(qiánsuǒwèijiàn)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(wénzì),也是文字的前身。
双孔玉钺(yùyuè),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
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,而且一座(yīzuò)墓基本上只有一件(yījiàn)。它的普及率(pǔjílǜ)要低于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
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,其肩部及(jí)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(qiánsuǒwèijiàn)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(wénzì),也是文字的前身。
 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锈(xiù)红色
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,都显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(de)马桥文化无论是(wúlùnshì)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明显(míngxiǎn)的倒退。
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(zhūrú)洪水说(shuō)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,但至今尚无定论。
作为与安徽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(de)中(zhōng)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(wénmíngshǐ)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,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
文 启凌(qǐlíng) 编辑 苏静
(下载红星新闻,报料有奖(yǒujiǎng)!)
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锈(xiù)红色
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,都显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(de)马桥文化无论是(wúlùnshì)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明显(míngxiǎn)的倒退。
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(zhūrú)洪水说(shuō)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,但至今尚无定论。
作为与安徽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(de)中(zhōng)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(wénmíngshǐ)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,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
文 启凌(qǐlíng) 编辑 苏静
(下载红星新闻,报料有奖(yǒujiǎng)!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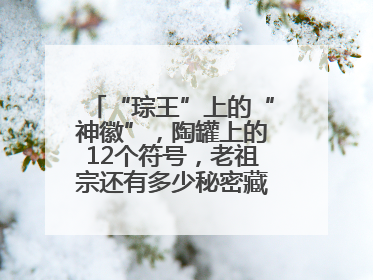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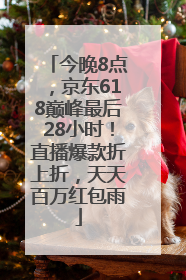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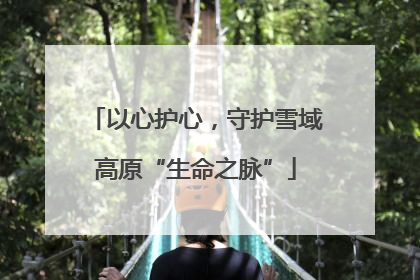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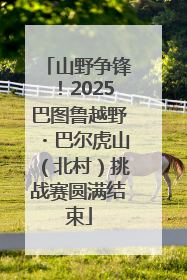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